最近武漢肺炎防疫時期,各大媒體不停宣導勤洗手的重要性。洗手,這個在我們學齡前就常被教導實行的衛生步驟,對一般台灣人來說應該都熟到不能再熟了。但你知道洗手可以消除病毒這觀念,在距今大概 170 年前,還是天方夜譚嗎?
170 年前,當時的醫療界還沒有清洗手上的病菌這樣的觀念,醫師在幫病患治療傷口時,經常有病菌透過傷口進入病患體內,造成感染死亡,這種情形在婦科尤其常見。當時的婦女分娩時,傷口被醫師沒洗淨的雙手碰過,對於分娩中的婦女來說是很致命的。
那個年代,因為醫護人員不洗手,導致接生以及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居高不下,病人寧願待在家煎熬也不願意進醫院。
當時有一名匈牙利婦產科醫師,名叫伊格納茲·塞麥爾維斯(Ignaz Semmelweis),他提出了讓醫生在看診之前,先將雙手洗淨消毒的觀念,可以殺死病菌的觀念,以降低病患死亡率。
這個說法一發佈,醫學界一片譁然,這等同於是在說病患的死亡是醫生間接造成的,並影射醫生不衛生、不專業,一夜之間塞麥爾維斯成了同行中的過街老鼠,人人罵人人打,而至於他提出的洗手說,更不可能在業界被實行。
等到醫學界認同他的學說,並推動勤洗手的做法時,已經是他死後幾十年,大約 1880 年前後的事了。
塞麥爾維斯初次發表學說是在 1850 年,以現今的 2020 年來看,還算是近代發生的事。你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議,這麼一個簡單正常的觀念,推行為何受到這麼大的阻礙?洗個手也不會讓醫生掉一塊肉的事,在當時為何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嘗試?
很簡單,因為「多數人」都不認同他,所以即使有少部份的人覺得這方法似乎可行,也不敢貿然去挑戰群眾的力量。
像塞麥爾維斯醫師這樣,發出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,我們稱之為「異見」(dissent),這類人通常有兩種下場,一種是一夕成名,一種是人人恥笑唾棄,很顯然的,他屬於後者。
異見者是相當容易受打壓的一群人,早期的社會封閉保守,太過大膽的主張或個人風格,容易被當作異類。當群體都做著同一件事,若有人提出不同看法,為了維護團體的「正常運作」,就會強制要求異見者跟著服從主流價值,別以為你的與眾不同會讓你變得很酷,俗話說槍打出頭鳥,你的特別會變成標靶,最顯目的攻擊目標。
無處不在的主流意識
別說 170 年前封閉的社會,就連現代人如你我,都可能當過打壓異見的那個主流派。
舉個簡單的例子,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,班上同學會將寶特瓶飲料罐放在桌子邊上一角,平時上課不喝,也會擺在那裡,沒飲料的則會放上自己的水壺(別問我為什麼,小學生的潮流現在的我無法理解),幾乎全班都這麼做,老師也從來沒阻止過。但班上在校內評比的整潔分數一直都很差,有天我們班上的一名李同學,在班會跟老師提出:「讓大家把桌面上的飲料收下去,看上去會比較乾淨整齊。」
老師採用了,當場叫所有人把寶特瓶收下去。班上同學一邊收,一邊嘀咕碎念:「很煩欸,都他啦,要收起來,不能放了。」
全班都無法理解李同學為什麼要做這麼「害大家不方便的事」,那陣子李同學被班上的一夥小圈圈帶頭欺負,他們欺負他的理由就是他在班會上打了這個報告。而那時沒有人幫李同學說話,因為全班都認為他做了讓大家不方便的事,他就是罪人。
即使李同學講的並沒有不對,依照規定,上課時桌面本來就不該放任何零食飲料,在這之前只是老師默許。但李同學依然成為被打壓的對象。
再舉個例子好了,幾年前我跟一票朋友約在某人家裡聚會,到了晚上大家聊說晚餐要吃什麼,於是提議叫外送。多數人都提議要吃麥當勞,因為外送費用好均攤(那時 Uber Eats 還不流行),這時某位朋友昀昀,提議點肯德基的某套餐,份量多比較划算,但一說出口,就被大家以「一起點麥當勞就好啦」、「幹嘛分兩批點」、「你要吃的東西麥當勞也有啊」各種說法勸退。
昀昀被大家輪番說了一遍,也就默默點頭,不再堅持,那一餐最後還是點了麥當勞。
聚會結束後,我和另一位朋友順路一起走回家,朋友突然問我:「妳不覺得昀昀很奇怪嗎?」
我:「奇怪?哪裡奇怪?」
朋友:「她很不合群啊,大家都說要吃麥當勞,她就說想吃肯德基。」
這個例子是不是備感孰悉?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在生活中,只要一個群體中,有人提出異議,就會被私下議論,在看到別人選擇挑戰主流價值時,甚至會有多數派的人因自己跟主流選擇一致而感到慶幸跟驕傲,並嘲笑那個做少數選擇的人。

查蘭.內米斯所著的《異見的力量》一書中有講到,多數人是一種很大的力量,會促使我們同意或追隨他們的腳步。群眾的力量很強大,且無所不在。
書中舉另一個真實發生過的空難事件,來讓人更深刻瞭解群眾的力量。1978 年,一架從紐約前往奧勒岡的聯航 173 號航班,當接近目的地、即將放下起落架的時候,飛機發出砰地一聲巨響,開始左搖右晃。機組人員開始檢查起落架或是其它部位出了什麼問題。於是駕駛員決定先不降落,讓飛機在天上盤旋一陣子,等找出問題再安全降落。
這段時間,駕駛艙內的飛航工程師講了一句:「我們還有 3000 磅燃油。」但機上每個人都在找起落架的問題,沒有一人把這句話放在心上。結果,還沒等到起落架問題查出,飛機就墜毀了,墜毀原因是燃油不足,導致引擎失靈。
當機上所有成員都已經有共識「先去做某件事」,那麼其他聲音就會被忽略。因為成員都會認為多數人認定的事才是要事。
破解多數盲從的「從眾效應」
很多人都會認為自己有獨立思考的能力,但面對多數人的看法時,自己卻很容易就順勢而為地同意了。
若是真心覺得多數意見是正確的而贊同也就算了,但有時沒有良好的論證,人也會輕易往多數的那一方靠攏,只因為那是多數人的選擇,「多數人」本身就是一個容易說服人的證據,會讓人產生一種認知--這麼多人都做了這個決定,那錯的機率應該很低。
如果一個團體裡,每個人都是經過獨立思考後做出決定,那他們的平均判斷就有可能是正確的。但如果是一群人互相影響,那一群人的正確度就跟一個人的正確度差不多。
人被群體決策影響而跟進的這種情況,被稱之為「從眾效應」(又稱「羊群效應」)。
但這並不代表你要刻意違背主流去做逆向選擇才叫獨立思考。重點不在於要不要反對多數,事實上,多數意見真有可能是正確的。只是我們不應該以數量做為依據,去判斷它的正確性。
無論主流價值如何,都應該抱持獨立的觀點去質疑每件事,最後你得出的結論才是你真正的想法,即使與主流相悖,也未嘗不可。
正確的異見,才有價值嗎?
聯航的例子裡,有一個極大的重點--在大多數人忙著找起落架問題的時候,異見者的忠告才是正確的。
如果異見是正確的,那麼異見者的聲音就有莫大價值,可如果意見不是正確的,就不存在價值了嗎?不,非正確的異見依然有它的用處存在。
共識會創造單一焦點,異見則能刺激多元想法。
意見可以打破盲從的現象,不論異見正確與否,去挑戰共識,可以刺激出更多面向的思考。
假使有 A 跟 B 兩派觀點,A 為多數,B 為對立的少數,當 B 在 A 的主場裡發表異見,除了出現贊同 B 的少部份人,還有可能引起某些人開始產生第三種 C 派觀點,接著多派一起討論溝通,得出比原本 A、B、C 三派都要更好的第四種結論。

出頭鳥的挑戰
說明了這麼多異見的價值,但作為一個異見者,本身是一件容易的事嗎?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
回到最開始說的塞麥爾維斯醫師的故事,他就是一個好例子。比起提出異見後彼此理解然後共同決策出更好的方向的情況,更常見的發展是:人們在聽見少數派的聲音時,會先開始發火。發完火後,就會開始辱罵、爭辯,質疑異見者的智力跟動機,甚至演變成人身攻擊。
多數團體因為有主流優勢,所以通常不需要對自己的選擇多加解釋,但異見者卻必須肩負「說服」的責任。
異見者在團體中通常不受歡迎,但只要有一人發聲,就會有其他異見者跟著起來附和,或許附和的聲音依然是少數,但這也是讓少數聲音慢慢增力的契機。
而當少數派開始有了一定聲量,這時異見者也必須擔任少數派團體中彷彿精神領袖一樣的存在,當一個異見者發揮自身影響力,集結了一群有共同信念的人,他就突然不被群眾允許再成為另一種異見者了。
這種情況以政治或學運領袖身分較為常見。
當他們提出第一種異見,表明了自己的當時立場,會有一群人認同這個理念而聚集在他身邊,但人的想法是會隨著時間改變的(如果一生都一成不變也是蠻可怕的),當他過去的異見成了主流價值,而他因為想法改變而再提出另一種異見時,基本上他的領袖生涯就宣告結束了。
這時的少數群體面對更少數的新異見,又成了相對的多數派,開始一輪多數打壓少數的循環。
人是群居動物,在群體生活中,很容易陷進團體共識的泥沼而不自知,團體中的每個人,多少都有掌握社會主流價值的控制慾,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,不管盲從還是獨立思考,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選擇毫不懷疑,即使它確實存在誤區。
對於少數異見的壓迫從來就不會少,一派已經是少數的異見群體,再遇到下一個更少數的異見群體時,壓迫同樣再次上演。
接著回來談談洗手的先驅者塞麥爾維斯醫師,下場令人唏噓。他最後被醫學界敵視排擠,被強制送往精神病院度過下半生,最後魂葬於此。
若是異見者能在社會中擁有一定友善的發言環境,或許可以讓這世界變得更多采多姿,並且出現更多突破既有框架的新選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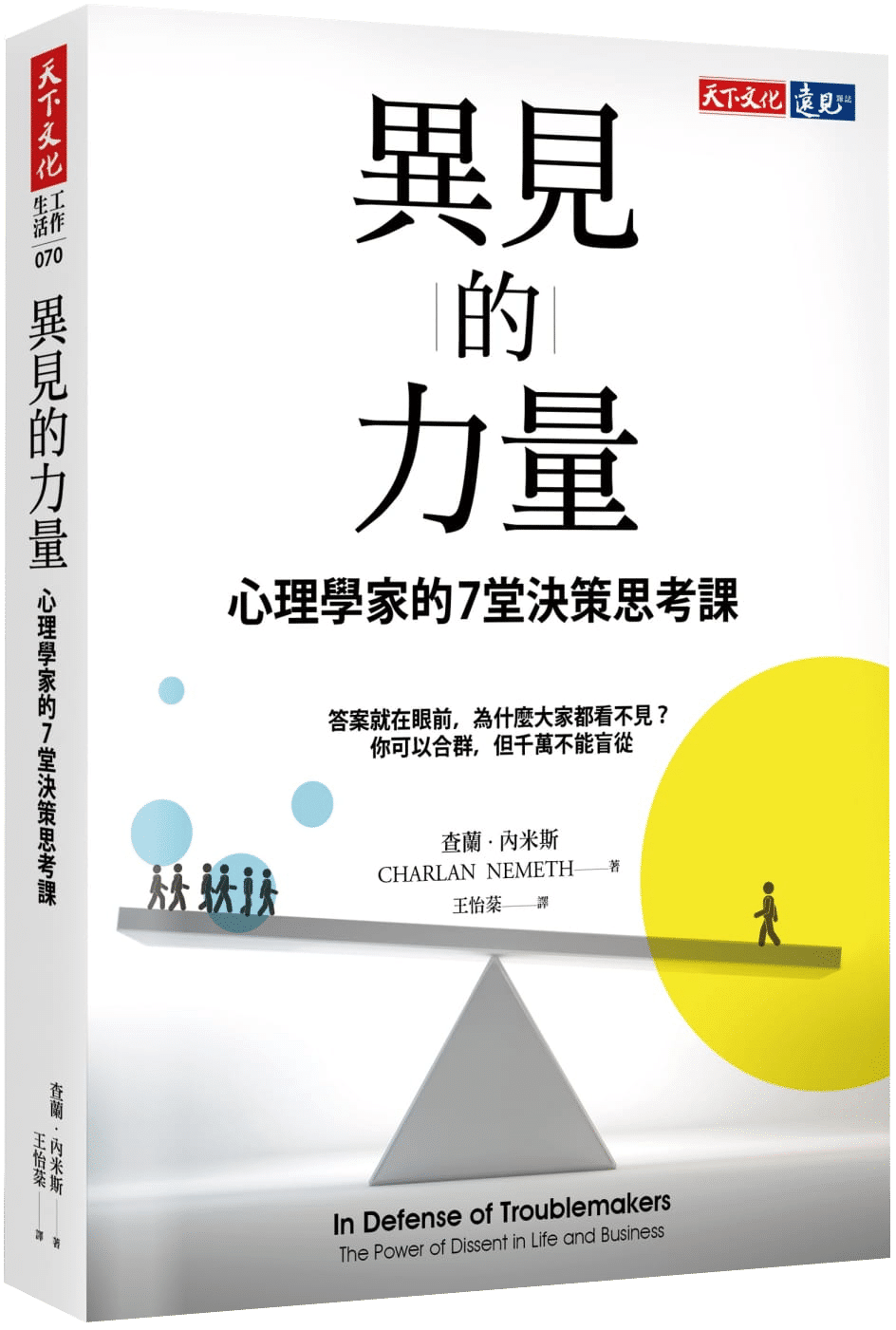
- 異見的力量:心理學家的7堂決策思考課
- 作者: 查蘭‧內米斯
- 譯者:王怡棻
- 出版社:天下文化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