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麼是人蟲?
人蟲,是先富起來的人玩的遊戲──買來的嬰兒將其困在封閉的空間,以自己對文化的興趣,對其進行單一的特殊教育,待其有獨立生存能力之後在將其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丟掉。
而後在觀察其在社會中的生存、自救能力,以比較自己認同的文化對社會制度的適應程度,並由此判斷這種文化在此制度下的好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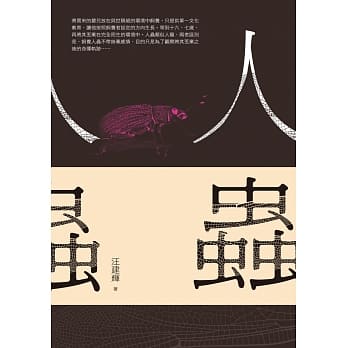
汪建輝的《人蟲》是一部虛與實、幻與真、過去與未來不斷交錯的小說,飄忽不定的時間線、一個個看似熟悉的陌生角色,藉由一個故事,多個角色觀點,觀察在專制社會下每個人的生活。
隨著越深入閱讀,離故事的核心越近,越對這個生病的專制社會感到恐懼。
被當作人蟲養大的女主角「芳鄰」,於她而言,世界的邊緣是豪宅的大門,她的大海是游泳池,她的海攤是沙坑。在被丟棄在戶外後,她才慢慢猜測到自己經歷過什麼。
為了理想,她逃跑過;為了自由,她掙扎過;為了生活,她墮落過,然而最終就如同她那瘸了腿的瘋子老公,逃不過命運的追殺。
她從豪宅裡人工打造的虛幻世界走入現實,她才發現過往的一切,都只是巨大的囚牢。
人蟲類似人寵,兩者區別是,飼養人蟲不帶絲毫感情,目的只是為了觀察將其丟棄之後的命運軌跡。
如果有天你也發現,現實是一個巨大的囚牢,你有勇氣逃離嗎?
在中國,人們沒有出版、言論自由,於是有很多不能說不能寫的,沒人敢碰,很多真實,都被忽略。
像是近期鬧得沸沸揚揚的反送中,你會發現大部分中國人與多數外界人的觀點是衝突的,其實不是他們愚忠,而是他們不知道。就像幼稚園殺手唱的:「中國的說法,中國有中國的說法。」。
他們不知道正確的訊息,因為他們收到的資訊不一定是真的;他們覺得反抗是胡鬧,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現在擁有的自由,其實只是放在展示櫃中精美的糖果,看的到吃不到;你覺得他們什麼都不懂還是一直大放厥詞,因為他們真正懂的人都不能發聲。

自由到底是什麼,或許擁有的你早就視其如空氣般自然而不以為意,然而沒有自由,就如同空氣一點點的被抽去,慢慢的失去思考能力,慢慢的被現實侵蝕,慢慢的服從命令。
這本《人蟲》有著不斷轉換的時空,其實不易閱讀,但在困惑與不解中,這本書就像一個巨大的謎團,引誘你讀到最後,像智力大考驗一樣,把所有碎片都連接成一個完整的現實。
最後你會發現,不只在專制社會,自稱民主國家的我們,也常發生一樣的現象。
或許你會情不自禁的想問:「我也是人蟲嗎?」

〈那個人〉:文化道德的桎梏,天涯海角追捕他的逃犯
其中一個短篇故事的開端,是由一份手稿開始的,那是一份村子首富在富起來前寫的文學作品。
〈那個人〉描述女孩為了躲避虛偽的社會而逃到海邊,在與一名男孩相遇後,以「母子」的關係互相扶持生活下去。從文明社會逃出的女孩避開了制度的綑綁、人性的邪惡,卻躲不開腦海裡被「文化」刻下的道德觀念。
在與代表「自然」的男孩平安共度十多年後,卻因為男孩的成長成人而自然產生的「慾望」、女孩腦中「倫理道德」的束縛,最終不得不離開這個她心中的「理想國」。

在海岸邊成長的男孩,過著日復一日單調的日子,穿著簡樸的衣服,沒有外界的物質誘惑,也享受不到這花花世界的五光十色。然而他是開心的,他乾淨爽朗的微笑,他用汗水換來的生活,他對外界的無知,都造就了他對目前生活的滿意。
這就好似我們看到一些在專制社會下成長的人們,多虧網路的發達,我們常在社群網站中看見與我們不同群體的人們在發聲,有些言詞句句在理,有些字句荒誕不經,但他們卻對自己的立場堅信不移。
你幸福,是因為不知什麼是幸福。
所以,不如就全部封鎖吧!只要沒看到、不知道,這些美好你從來沒想像過,你就會恪守本分,沿著從小被教育的道路,安穩地走下去。或許這就是創造人蟲的意義,要改變、懷疑自己從小到大接受的思想教育,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。
其實不只是在專制社會,身為台灣人的我們,也一直有這樣的通病。台灣長期處於兩黨獨大的政治氛圍,加上如今社群軟體造成同溫層的不斷加厚,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們在了解前都習慣先否決他人的思想。

只要意見不一,總是覺得對方不可理喻、入魔、腦粉,年輕人遇到立場不同者就認為是對方是老人固化的思想、只要親中就覺得是被金錢迷惑腦袋、覺得支持多元成家就是離經叛道。
厚厚的同溫層中,我們總是在深入了解前就先行阻擋訊息傳入,不願聆聽對方的聲音,怒罵立場不同的族群,然後大喊我們是民主國家,尊重每個人的言論自由。其實,我們只是處於不同的容器中的井底之蛙罷了。
處於小容器裡的人嚮往著大的容器,以為那就是自由;位於大容器裡的人則瞧不起小容器裡的人,認為他們的格局太小。
小容器裡的人向外看、大容器裡的人向裡看。他們逃不出這個封閉的大容器,這就是我們共同的悲哀。
人蟲芳鄰:被社會體制囚禁的自由靈魂
《人蟲》的主視角,草根作家「我」,在梅花寨遇見了本書的女主角──芳鄰,如今,她是一名妓女。
當初〈那個人〉並沒有寫完。那位村子裡的首富在富起來後,再也寫不出東西來了。
於是他的大兒子為了討他歡心,把〈那個人〉的故事搬到現實中,把買來的女孩關在豪宅裡,與世隔絕,聘請家教教導他所偏好的思想文化,再把她丟棄。那個她,就是芳鄰。
這個世界很奇怪,文學往往和困苦綑綁在一起。生活一旦過的好了,心靈也就被油葷給堵塞住了。
幾經波折後,為了養活瘋子畫家老公──鬱和女兒,她成為了一名妓女,但她不以此為羞恥,因為她只賣肉體,不賣靈魂。
芳鄰是潔白的,雪白的皮膚,發亮的雙眸,飄逸的長髮,她善良美麗的讓所有人渴望,純真笑容被所有人覬覦。
然而在被故事中的一位作家「本本」諷刺沒有羞恥心後,她的純真潔白消失了,剩下的是大家所期望看到、與文學作品中相同的──空洞、空無、失神的妓女形象。
「你們是作家,你們決定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的。你們的手上拿著一根準繩,圈成上吊自殺時的那種形狀,一個一個的套在人們的脖子上,去規劃別人、引領別人……」
社會中的文化層次由理念、制度、器物所構成,理念這個層面最虛無也最難以改變,但若是下層的制度實施多年而影響到理念,帶給社會的影響絕對是全面且根深柢固的。
像是「貼標籤」這個舉動早已在人類社會中存在多年,就如同有時候道德倫理印在我們腦中的那條準繩,才是真正的殺人武器。
「一個叫花子之所以成為叫花子,其一是他的行為使他成為叫花子,其二是別人把他視為叫花子。只有這兩者合一了,叫花子才會成為真正的叫花子。」
寫作的意義:下半身寫作 V.S. 時代文學
汪建輝認為:「人類自有文明以來,對物質世界的認知是由鬆散轉為嚴謹,而對生活中道德的認識則是由嚴謹轉為鬆散。」
隨著文化世界與物質世界呈互補關係,每個時代都有其代表的文學,唐詩宋詞元曲,而現在社會在人類滿足溫飽後,相對的文學有兩種,一種是性、一種是政治。
在專制社會下,政治這條路是被堵死的。於是人們往性發展,從事下半身寫作,其實不只文學,藝術亦如是。
小說中「鬱」的前情人梅子,用自己的身體蒐集了13個男人的精液,代表耶穌的十三門徒,放在骨灰盒裡埋在橄欖樹下,命名為《末日審判》,最終享譽國際。
然而認真的人總是輸的,「鬱」想走思想路線,最終賠了一隻腿,變成藝術圈的笑話,什麼都沒獲得。

而草根作家「我」也是如此,比起獲得政府認證的作家「本本」,他沒錢沒身分,卻一直堅持寫自己所認為最真實的寫作。或許這正是本書作者汪建輝想為自己說的話,在不自由的年代,他只能孤獨的繼續堅持這條路,為了讓別人看到這社會底下真實的面貌。
「如果黑暗的時間很長,耗費了一代人的生命,那麼未來豈不是沒有人知道曾經有過的黑暗?等到民主再寫,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在專制社會下,人們不敢碰真實的政治,只往純文學、下半身文學發展,還以為自己有了完全寫作的自由。
就像拿著官方協會作家證的「本本」瞧不起那些沒拿證的草根作家,認為他們沒實力;草根作家「我」則瞧不起那本作家證,認為專制底下唯一的正氣就是反革命、反專制,認為有敵人的寫作才是真正的寫作。
究竟那個才是這時代的文學?
若以人數論,下半身文學會是這時代的代表文學;但若以價值論,政治文學才能在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。但大家都知道,這是個重量不重質,多數人贏過少數人的年代,誰會造成轟動、誰會成為主流,結果不言而喻。
「爬出來吧,給你自由」這是過去的標本
「跪下去吧,賞你骨頭」這是現在的範例
《人蟲》這本看似荒誕不可信,然而這卻是在極權社會中真真實實發生的。為了告訴世人事實的真相,汪建輝縱使作品不曾在中國出版,也不曾獲得名聲,他只是繼續寫著,用耐心毅力,孤獨地把這些真實的碎片,用虛構連接起來。
這是一個精神比矮的年代,究竟有誰能夠站著,又把錢給賺了?
- 人蟲
- 作者:汪建輝
- 出版社:釀出版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