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發生的這幾個月,人們的心理對待權威的態度正在改變,這反過來改變了人們自身。用精神分析的話來說,主體與大他者的關係決定了主體性的運作模式。
科學社群的權威性受到了質疑。這幾個月來,科學論述的爆增並沒有緩和人們對疫情的不安,反而是加劇恐慌。
如法國著名病毒學專家、諾貝爾獎得主呂克·蒙塔尼耶(Luc Montagnier)前幾日公開發表「病毒人造論」,掀起法國科學界一波爭議,因為目前多數學者認為病毒應該是自然演化的結果。
科學社群內部論述上的不一致,使得人們對科學家的權威性產生懷疑,到底我們該相信誰說的?
並且,在傳播感染上,人們看到科學家也難以倖免,3月18日,英國首席流行病學家尼爾·弗格森(Neil Ferguson)出現了武漢肺炎症狀,開始自我隔離,如果連流行病學家都自身難保,民眾又該如何是好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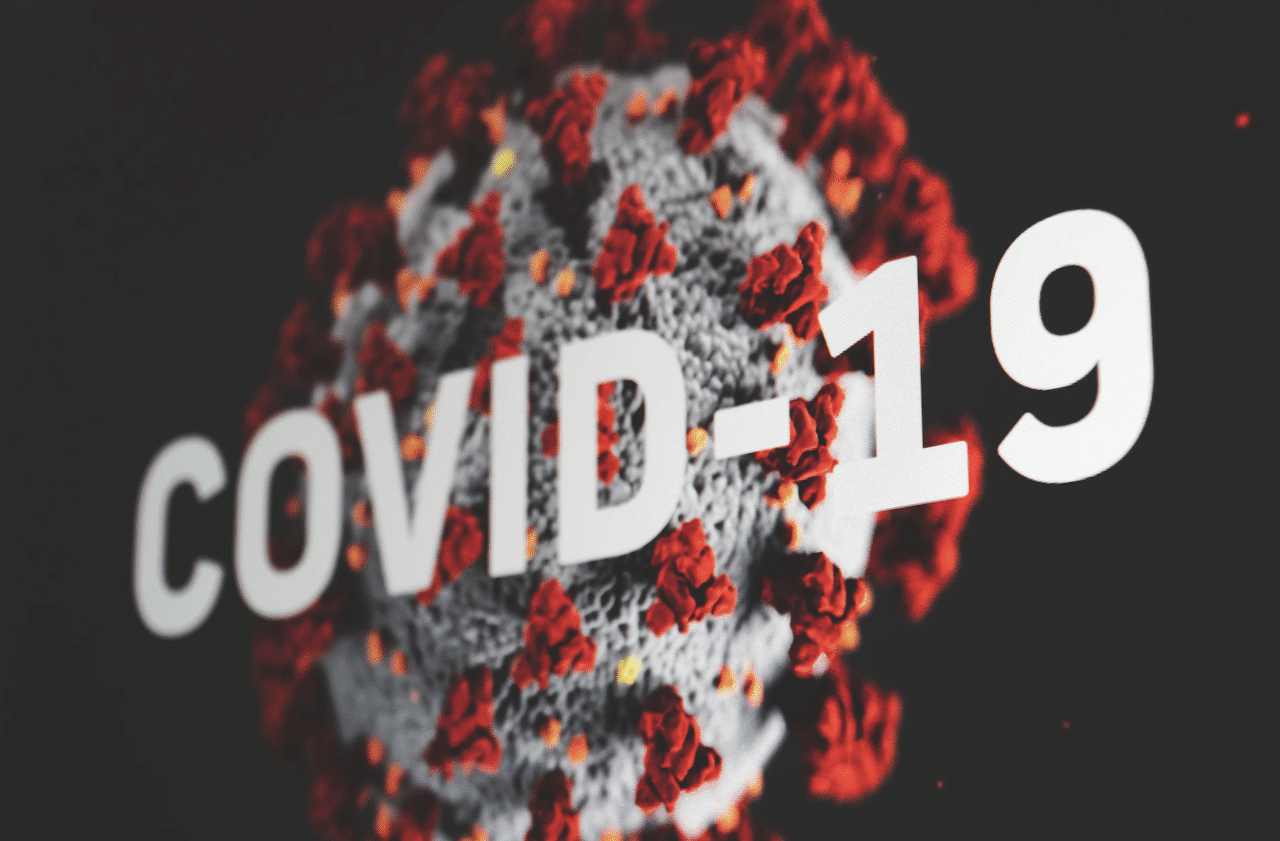
對權威組織的不信任,對你我的心靈造成巨大影響
人們充斥著對組織權威的不信任。
在國內,中華民國海軍艦隊在4月19日爆出24人確診,國軍成為防疫破口,還在全台走透透,國民開始擔心國防部隱匿疫情,連蔡英文總統也在4月22日出面公開道歉。
在國際上,則是世界各地都激起了對WHO的反感,川普決定暫停資助過度傾中的WHO,台灣疾管署在去年底即通報WHO,警告新冠肺炎可能人傳人,近日卻遭WHO發言人譚德塞否認。
(我們不妨回想一下2003年SARS疫情爆發之初,在卡羅•厄巴尼醫師(Carlo Urbani)通報後,WHO即刻向全球發佈警訊,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有多大。)
在死傷人數最嚴重的義大利,佛羅倫斯大學流行病學家Sergio Romagnani所協助處理的威內托(Veneto)疫情之所以得以控制住,就是因為一開始沒有遵照WHO的指示,Romagnani甚至直言:WHO過於官僚化而缺乏實際處理病毒爆發的經驗(註1)。
科學社群、國家、國際組織,這些相對於個體的大他者,都在這場疫病中暴露出自己是不再可靠的權威。這對個體心靈產生了什麼影響?

焦慮,侵入你的意識與潛意識
首先,是主體的焦慮惶恐顯著大增,世界各地民眾責罵政府為何不做普篩,有可能各國早已遍佈無症狀感染者。
我有一個朋友身體發燒不適,懷疑自己可能得了肺炎但又不確定,但他可以確定的是,如果去檢測站被感染的機率會更大!
那麼到底該不該去做檢測?這種不確定性源自於病毒本身的特性,因為感染者可能沒有症狀,而有症狀者卻可能沒有感染,而焦慮就是源自於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過於模糊,彷彿介於有跟沒有之間。
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說:「焦慮並非沒有客體(n’est pas sans l’avoir; not without having),而是在客體所在之處,它沒有被看見。」(註2)
這可能是,對於無症狀感染者容易產生焦慮的最佳描述,名為Covid-19的朦朧客體在我身上,但我卻看不見,它並非沒有在那裡…
這種焦慮不安甚至已深入人們的潛意識,法國精神分析師Marie-Hélène Brousse的個案告訴他(註3),自己夢到他在撤離各種場所的景象 (vider les lieux),在法文中,撤離(vider)這個字宛如covid19的符號變形。
這個案例體現了佛洛伊德早已發現的夢的特徵,「日有所思,夜有所夢」,並且,夢境的變形方式是語言符號的拆解轉喻,也體現了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的名言:「無意識有像語言一樣的結構」。

搶購衛生紙,只因退化成巨嬰?
群眾焦慮發生後,接踵而來的是訴求安全感的個體化行動。民眾開始囤積各種物資,衛生紙之亂在世界各地發生,問題是為什麼要囤積衛生紙?
連搶購者自己也答不出來。從精神分析的觀點看,許多人似乎出現了臨床上常常可以觀察到的退行現象(regression),亦即在遭逢生命受挫時退回到生命中較早期的階段。
而在當前權威已經失落的時刻,退行到幼兒囤積癖的階段,彷彿給民眾一種主控權的安全感,就如同在肛門期的兒童會透過如廁訓練來確認自己的主控權一樣。
陰謀論謠言四起,因為你需要「確定性」
權威衰退後最值得研究的,莫過於對陰謀論的渴望越來越強烈,根據統計,美國現在有三成民眾相信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陰謀論(註4)。
世界各地的網友瘋傳新冠病毒是源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的消息,在3/16美國總統川普在Twitter上直稱新冠病毒為「中國病毒」,中國網民也不甘示弱回擊,指控病毒發源地是來自美國的實驗室。
這些看似沒有確切證據的陰謀論,若仔細看卻又都能自圓其說,如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團隊提取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曝光、美國去年流感狀況異常、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德特裡克堡(Fort Detrick)去年七月又突然關閉。
在沒有實質證據前,每個人都可以相信自己想相信的。
關鍵是這些各自競爭真假的陰謀論,背後的主體運作模式其實是相同的,也就是對確定性的追求,因為權威的大他者已經無法擔保知識的確定性。
佛洛伊德認為這就是人為什麼需要宗教,他觀察到兒童第一次見證到父母的權威性坍塌的時刻,兒童感到的驚慌不安,他必須尋找一個新的權威、一個像記憶中的父母親一樣偉大的替代品,所以「人格化的神不過就是心理上崇高的父親」(註5)。
有宗教信仰的人,在這次的疫情中也許比較沒那麼惶恐不安。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,主體的心理狀態則變得越來越趨近妄想症(Paranoid)。
例如,在歐洲有一派的陰謀論者認為,新冠病毒是靠5G網路傳播,因為非洲沒有5G網路基地台所以才沒有疫情爆發,更有荷蘭民眾到當地基地台縱火,這種情況也可以在許多被迫害妄想症病患者身上發現,他們認為政府其實是邪惡組織,會透過無線電洗腦人民、灌輸人民恐怖思想。
妄想症的主體在想像的世界裡獲得確定性的滿足,而其前提恰好是對於真實世界的完全質疑。
在此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:陰謀論的主體恰好就是笛卡兒主體。懷疑一切!尤其是一切權威告訴民眾的知識。
這不就是理性思考的本質?笛卡兒認為這會帶人類通向理性真理的道路,如今卻是走向了陰謀論大戰的亂局…
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,在疫情中反轉
如果說正常人變得越來越不正常,那麼診療室裡發生的事情恰好相反。
加拿大的精神分析師Don Carveth觀察到,原本在進行療程的多個個案,也因為疫情爆發後發生了改變(註6)。
幻想症患者的情況變好了,因為人們開始變得跟幻想症患者一樣猜忌多疑、追逐陰謀論,深怕自己檢測出感染的話,自己過去影響到哪些人。
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情況也變好了,因為全世界的群眾都開始變得歇斯底里,對身體的敏感度提升,只要體溫超過37度、咳嗽一下、身體不適,就極度擔憂是染上了肺炎。
強迫症患者的情況也變好了,因為現在大家都得了名為瘋狂洗手、噴酒精的強迫症。
當原本的「正常人」都彷彿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、歇斯底里症、強迫症時,診療室裡的病患反而好了起來,原本自認為病態的,現在變為正常了。疫情改變了日常規範的同時,也改變了主體的病識感。

總結的說,我希望指出在這場疫病中,人們的心理變化並不是源自於疫情本身的嚴重性,而是源自於人們與權威大他者(科學社群、國家、國際組織)的關係改變了。
這些關係的改變才是主體性改變的根源(焦慮惶恐、尋求安全感、渴望陰謀論),而當統計上的多數人的主體性改變時,也連帶的改變了那些被視為不正常的人的主體性。
在這場瘟疫結束後,人們能夠重新看待什麼是正常,什麼是不正常嗎?
註解:
註1:INTERVIEW TO SERGIO ROMAGNANI “Veneto is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because it hasn’t followed the WHO”
註2: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: Book X : Anxiety : 1962-1963. P.89
註3: Marie-Hélène Brousse, The Times of the Virus
註4: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us-news/2020/apr/13/coronavirus-conspiracy-theory-laboratory-report?CMP=fb_gu&utm_medium=Social&utm_source=Facebook&fbclid=IwAR0LG1M6Y5QpIkYs1Yn3eiHGziEzohy5-d5J4wlUeqGQHSz1AZIes3cUvAo#Echobox=1586806130
註5:佛洛伊德《李奧納多.達文西及其童年回憶》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.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, Volume XI (1910):
註6: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NqZmV02vbQ&t=3s






